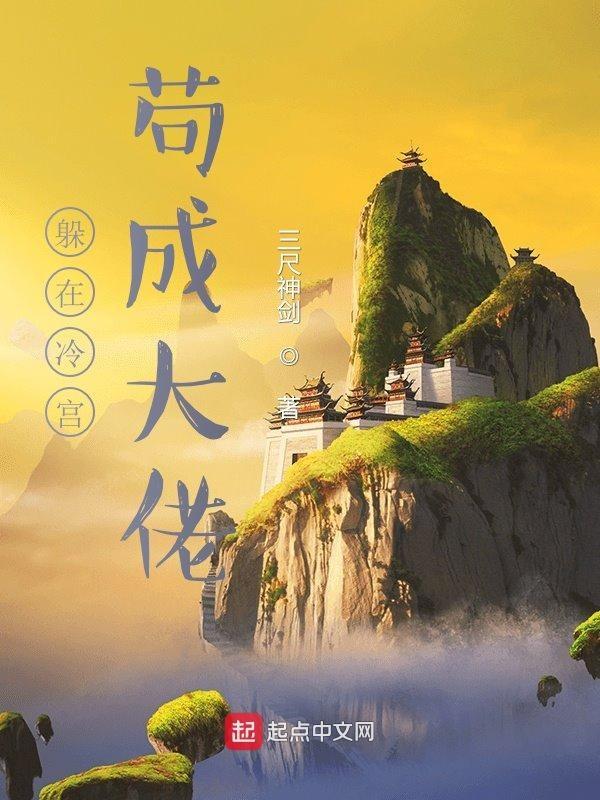文海阁>与“反贼”破镜重圆了 > 第84章(第2页)
第84章(第2页)
春松又道:“这些年这些话藏在心里,奴婢无一日能喘息。奴婢罪孽深重,今日见公子,方得解脱。”
傅徽之心中一凛。他看着春松面朝坟茔慢慢起身,也不由望向坟茔。
坟茔外砌有砖石。
傅徽之立刻明白了。人若撞上去,怕是会血溅当场。
傅徽之当即向坟茔扑去。下一刻,前胸便不受控制地撞上砖石,而后背也是一阵剧痛。他甚至听见自己后背的闷响。
这丫头当真是下了必死的决心。
好在他已养了近二十日的伤,应当不至于被这一撞撞出血来。
春松见自己竟撞在自家公子的背上,惊呼:“三公子!”
她急忙去扶傅徽之,哭道:“为何要救我……我该死,早该死了……”
傅徽之缓过痛后慢慢转过面来:“你若想死,为何非要等到见过我。”
“我不能独自一人死了,必须有人知道我的罪孽。况且,我也是想挽回的。但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为时已晚。”
傅徽之叹道:“不晚。”
春松怔怔地问:“当真么?”
傅徽之又问当年玉佩之事究竟如何,春松细细说了。
“当年作证,你必是在大理寺、刑部官吏前露过面了。若你改易证词,自是对翻案有利。只是……”傅徽之有些犹豫,“若如此,你怕是难逃罪责。”
春松立即道:“便是因此获死罪,我也甘愿。”
“容我再想想……”傅徽之又问春松现居何处,春松也答了。傅徽之犹豫了一回,还是让春松自回宿处。又提醒她近日外间不太平,少来坟茔处。
“三公子,便让我跟着你罢。”春松道。
“我处也不安稳。我若有事,自会去寻你。”傅徽之道,“只一点,活着方可行事。莫再如此。”
春松自是知道如此是哪般,应道:“我皆听公子的。”
傅徽之在傅时文坟前设奠、叩拜毕,转身欲去时,春松忽又问:“三公子,你怪我么?”
傅徽之轻叹一声:“你毕竟不是伺候我的。二哥在此。你最了解他,当知他若在时,会否见责于你。”他最后一字字道,“我心与兄同。”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去。
春松怔了许久,忽又跪地,在空阔的郊原上放声大哭。
音甚凄恻。
傅徽之的步子只停了一瞬便又向前迈去。
…………
言心莹偷偷去见邱淑,得知她父兄皆不在府中。但知道一家人都没事她便放心了。
言心莹又将襄阳郡公之事告知邱淑,叮嘱邱淑要提醒父兄出门时多带随从护卫。府中夜里守卫也不可松懈。
而后言心莹又去了燕国公府。她阿舅自然也不在,只外祖父赋闲在家。她几乎将同邱淑说的话尽皆对邱平说了一回。
邱平又说邱瑞明日不当值,言心莹便想着今日先回,明日再来。这襄阳郡公谋反之事,定要当面与邱瑞商议商议。
言心莹骑马出城,到村中宅舎时,天色已晚。
白潏露早回了,说主人安好,客舍一如往常。
而后言心莹进了傅徽之的屋子,看见了他。比起白日分手时,傅徽之似乎又多了什么心事的样子。
傅徽之后背的伤虽已不用缠软帛,但言心莹每日还是会习惯性察看下他的伤处。
将傅徽之衣服褪下后,言心莹不由轻轻嘶了一声。
傅徽之心道要糟,本以为养了二十日伤,不至被春松撞出血。他自己也无法看后背确认。眼下看言心莹的反应便知还是被撞出淤血或青紫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