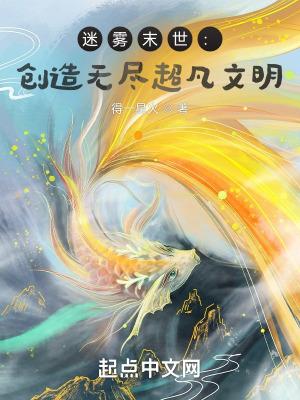文海阁>仅他可见 > 第79章 我只要一个絮林(第1页)
第79章 我只要一个絮林(第1页)
教教我。
教他?
可,怎么教呢。为什么要教?
絮林低着头,看着枕在自己膝盖上,紧紧抱着自己的纪槿玹。
他眼尾滑出的那滴水温热,黏在絮林皮肤上了,烫得仿佛要撕下他的一层皮。
纪槿玹这样的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哭泣?会在什么人面前露出这般脆弱的神情?
不止一次,絮林见过。
三年前,纪槿玹因为腺体受损,没有他的信息素,被五花大绑在病床上,絮林给他提供了信息素,离去时,迷迷糊糊的纪槿玹曾开口挽留他,恳求过他。
三年后的现在,纪槿玹又一次成了那时的他。
三年的时间没有治愈纪槿玹的病情,他好像病得更重了,快要死了。
或许,絮林该像那个时候一样掉头就走,可是——
地下室里灯光朦胧,氤氲的暖光披在絮林的半个身子上,这一小片地方很安静,只听得到絮林和他两道几不可闻的呼吸声。
他被纪槿玹的两只手臂环着,桎梏在原地。
纪槿玹现在不清醒,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力道。絮林不想和他说太多,也没有时间和他说太多。
他这个样子,一定得去看医生了。
“你先松开,我去给你叫人来。”
找不到抑制剂,自己的颈环也打不开,那就只剩下去找医生这一条路了。
纪槿玹不肯松。
怕松了,絮林就走了,再也看不到了。
实际上,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明天,絮林就会从丹市的土地上离开,再也不会踏足。即便踏足,也不会是来见纪槿玹。他们不会再遇到了。
所以,谈何补偿呢?
——他根本不需要纪槿玹的补偿。
“你恨我……”纪槿玹更加把脸往絮林的小腹上贴,声音闷闷地响:“恨我几年,十年,二十年,永远,都没关系。”
“我想,留在你身边。”
纪槿玹攥着他衣角布料的指骨泛着白:“让我,看到你吧。”
“只要能看到你,就足够了……”
絮林顿住,一时无言。
纪槿玹的身体冷得像冰,呼吸却烧得灼人。
他抱着絮林,嘴里喃喃着说着颠倒的话。
他把絮林十三区的房间原封不动地造在丹市这个小地下室里,安了一个除了他谁都进不来的门禁,难受的时候,抱着他一件早已没有味道的旧衣服,就这么在无人知道的地方安静地熬着。
熬过去了,皆大欢喜。
要是,熬不过去呢。
絮林垂眼,耳边是纪槿玹紊乱急促的呼吸。他躺在满地散落的药片中,无意识中仍在恳求着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