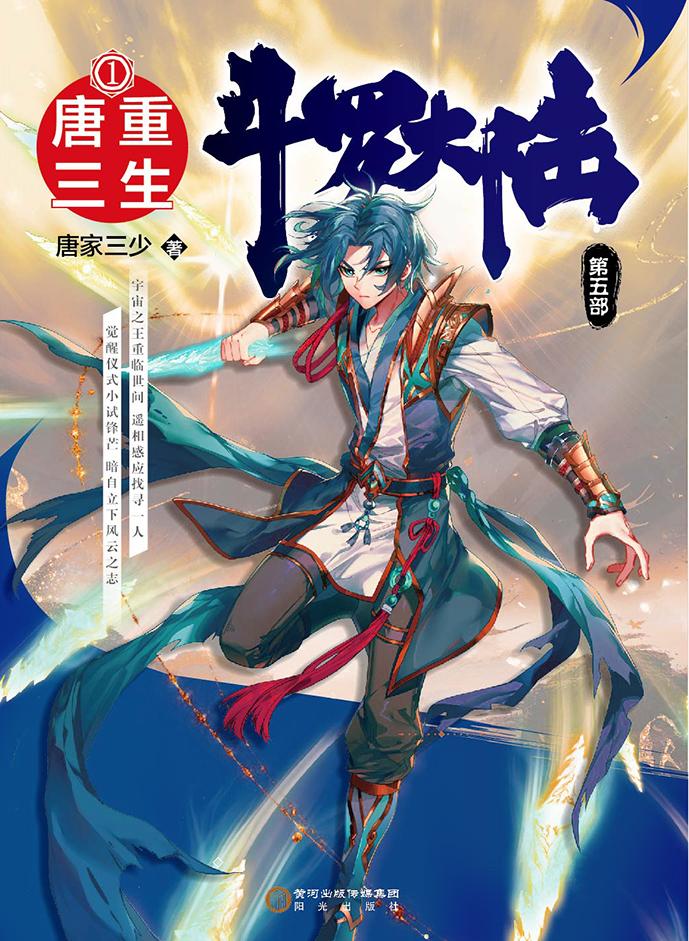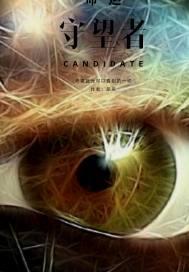文海阁>意识上传中 > 谎言空间中的不稳定轨道(第1页)
谎言空间中的不稳定轨道(第1页)
谎言空间中的不稳定轨道
我一向觉得在高速公路上睡觉最安全,至少是在某些路段上,只要它们位于周围吸引子[1]之间近乎平衡的区域内。我们的睡袋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北向双车道之间的褪色白线上(也许是因为从南面传过来的一丁点儿风水知识,还没有被从东面传来的科学人本主义、从西面传来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和从北面传来的反灵反智的享乐主义淹没),我可以安全地闭眼休息,知道等玛利亚和我醒来时,不会全心全意且不可逆转地深信教皇永不犯错、盖亚拥有感知能力[2]、冥想能诱发洞察力的幻觉、报税表能奇迹般地治愈疾病。
因此,当我醒来发现太阳早已爬出地平线,而玛利亚不在我身旁时,我并没有惊慌。没有任何信仰、世界观、宗教体系或文化能在夜里伸出魔爪,把她据为己有。吸引域的边界确实会波动,每天几十米地前进或后退,但任何一个吸引域都不太可能穿透到我们宝贵的无政府主义和怀疑论荒原的腹地来。我无法想象她为什么会离我而去,连一句话都没留下——但玛利亚时常会做我认为完全无法解释的事情,反过来也一样。尽管我们已经相处了一年,但情况依然如此。
我没有惊慌,但也没有逗留。我不想掉队太远。我爬起来,伸个懒腰,尝试判断她朝哪个方向走了。这个问题差不多等价于问我本人想去哪儿,除非她离开后此处的状况有所改变。
你无法对抗吸引子,也无法抵挡它们——但你有可能在它们之间找到一条通道,利用相互之间的矛盾来导航。最简单的起步方法是利用一个强大但足够遥远的吸引子来积蓄动量,同时注意安排好路线,以便在最后时刻利用一个反作用力来改变方向。
选择第一个吸引子,也就是你必须假装投诚的信念,这永远是个怪异的勾当。有时候它就像字面意义上的闻风而动,像是追寻某种外在的线索;但有时候它又像纯粹的内省,像是在尝试确定“我自己”真正的信念……有时候,想要区分这看似对立的两面本身就仿佛是一条歧途。对,他妈的禅意十足——此刻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它本身就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此处的平衡非常微妙,但有一股影响力稍微强大一点儿:就我的立场而言,东方的哲学无疑比其他信念更有说服力,知道这一点纯粹来自地理原因并没有让它变得不再真实。我对着公路和铁路之间的铁丝网撒尿,希望能加速它的朽烂,然后我卷起睡袋,对着水壶喝了一口,背上行囊,开始步行。
一辆面包房的自动送货车从我身旁疾驰而过,我咒骂我的孤独:若是不经过精心准备,想要利用这些卡车,你需要至少两个身手敏捷的人,一个挡住车辆的前进路线,另一个负责偷食物。盗窃导致的货物损失数量并不大,因此被吸引子俘获的人能够容忍;想必只是不值得使用更严密的安保措施吧——不过毫无疑问,每一种道德的单一文化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理由”不把我们这些没有道德的流浪汉饿得只好屈服。我掏出一根病恹恹的胡萝卜,这是昨晚我经过我的一个蔬菜园时挖的。拿这东西当早餐也够可怜的,我一边啃胡萝卜,一边想象等我和玛利亚团聚后能偷到手的面包卷,我的期待几乎战胜了此刻啃木头般的寡淡口感。
公路和缓地转向东南。我来到一块夹在废弃工厂和荒弃住宅之间的土地,在相对寂静的背景之上,现在位于正前方的中国城的牵引力变得更加强大和明显了。当然了,“中国城”仅仅是个顺口的标签,而标签永远是一种过度简化;在大融合之前,那块区域容纳着至少十几种相互不同的文化,除了中国香港人和马来西亚华人,从韩国人到柬埔寨人,从泰国人到东帝汶人,一应俱全——还有从佛教到伊斯兰教的各种宗教的多个变种。多样性现在已经消失,对于大融合前那块区域的任何一个居民来说,最终稳定下来的同质混合物恐怕都极为怪异。当然了,对于现在的那些市民来说,这个奇异的杂交体无疑是完全正常的。这就是稳定的定义,也是吸引子存在的本质原因。假如我径直走进中国城,我不但会不由自主地拥有当地的价值观和信仰,还会乐于在余生中保持那个状态。
但我不认为我会径直走向那里,正如我不认为地球会径直坠入太阳一样。大融合已经过去近四年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吸引子俘获。
对于那天发生的种种变故,我听说过几十种“解释”,但我认为其中大多数都同等可疑——因为它们源自某些特定吸引子的世界观。我有时候会想到的一个解释是,在2018年1月12日,人类肯定跨过了什么不可预见的门槛——也许是全球总人口数——因此引发了突如其来、不可逆转的精神状态的剧变。
心灵感应不是个正确的字眼。毕竟,没人发现无数个咿咿呀呀的声音汇成海洋淹没了自己,也没人遭受同理心过载的痛苦折磨。意识的一般性叽叽喳喳依然被锁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平凡的心灵隐私并没有被打破。(或者,按照一些人的猜测,所有人的心灵隐私都被彻底打破,我们瞬生瞬灭的念头加起来构成了一块无特征白噪声的毯子,遮盖了整个地球,而大脑能够毫不费力地过滤掉它。)
原因暂且不提,总之谢天谢地,其他人的内在生活(就像以秒为单位的肥皂剧)和以前一样遥不可及……但对于彼此的价值观和信念、彼此最深信不疑的事物来说,我们的脑壳变成了一戳就破的肥皂泡。
刚开始,这意味着天下大乱。当时的记忆十分混乱,仿佛一场噩梦;我在城市里乱走了一天一夜(我认为),每六秒发现一个新的神(或类似的东西)——我没有看见幻象,也没有听见灵音,但不可见的力量以做梦般的逻辑把我从一个信仰拉向另一个。人们在恍惚中走动,缩头缩脑,跌跌撞撞——而理念像闪电似的在我们之间跳跃。一个天启过后是另一个相反的天启。我无比希望这样的情况能够停下——假如一个神保持不变的时间能足够我向他祈祷,我肯定会祈求神让这一切立刻结束。我听过其他流浪者把这种最初的神秘激变比作嗑药后的心理活动或**的**,比作被十米高的浪涛抓住又抛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接连不断——但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段经历让我想到最多的是一场严重的肠胃炎:在那个漫长的夜晚,我发着高烧,时而呕吐,时而腹泻。我全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和每一个关节都感到酸痛,皮肤烧得发烫。我觉得我要死了。而每当我想到自己不会有力量再从体内排出任何东西的时候,又一阵**就会从天而降。到了凌晨四点,我的无助像是完全超越性的:肠蠕动反射就像某种严厉但本质仁慈的神灵,占据了我的存在。就当时而言,那是我最接近宗教体验的一段经历了。
在整座城市里,相互竞争的信仰体系在争夺效忠者,同时突变和杂交……就像你在实验中释放电脑病毒的随机种群,让它们彼此对抗,以证明演化论的精妙之处。情形也像同一些信仰在历史上的碰撞,但在新的互动模式之下,其长度和时间跨度被大大缩短,也少流了许多鲜血,因为理念现在可以在纯粹精神的竞技场里战斗,而不是通过挥舞利剑的十字军战士或种族灭绝的集中营。或者,就像在地上释放了恶魔大军,让它们去抢占除义人外的所有心灵……
混乱持续得并不久。在一些地方,由于大融合前文化自身的聚集;在另一些地方,仅仅因为概率,特定的信仰体系获得了足够的先发优势,因此能够从信众构成的核心向外扩散,进入周围尚未涌现主导信仰的随机分散区域,俘获了相邻地点的失序群体。吸引子滚雪球般征服的疆域越大,它们成长得就越快。幸运的是,至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任何一个吸引子能够不受控制地扩张;它们或迟或早,最终不是被同等强大的邻居团团围住,就是因为处于城郊或邻近人烟稀少的非居民区而缺少足够的人口。
大融合后的一周内,无政府状态多多少少成了主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不是迁移就是皈依,最终都满足于其所在的位置和身份了。
我凑巧落在几个吸引子之间,尽管受到多个吸引子的影响,但没有被任何一个俘获,从那以后,我一直竭尽全力停留在轨道上。无论其中的诀窍是什么,我似乎都了然于胸。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流浪者的队伍越来越稀少,但我们的核心依然是自由的。
刚开始那几年里,被吸引子俘获的人会派无人直升机在城市上空撒传单,用各自信仰的隐喻描述先前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为灾难精心选择一个类比就足以说服他人皈依。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过了一段时间醒悟过来,书面文字作为布道的载体已经过时,视听技术亦然,但有些地方的人还没有承认这个事实。不久前,在一座废弃的屋子里,玛利亚和我用一台电池供电的电视机收到了来自理性主义者飞地广播网的信号,用彩色像素根据几条简单数学规则相互吞噬的舞蹈来“模拟”大崩溃。评论员喷吐自组织系统的各种术语——看啊,何等神奇的马后炮!闪动的色块迅速演变成熟悉的六边形蜂房模式,一个个蜂房被黑暗的壕沟隔开(那是无人居住的区域,只有几个几乎看不见的无足轻重的斑点。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在哪儿)。
本已存在的机器人与电信基础设施允许人们不离开所在的吸引域也能生活和工作,我不知道假如没有它们,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吸引域能确保你可以安全返回中央吸引子,其中大多数的宽度仅有一两公里。(事实上,肯定有很多地方不具备这么好的基础设施,但过去这几年,我一直没有接入世界村,所以我不知道那些地方现状如何。)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我比居住在它多个中心的人更依赖于社会的财富,因此我想我应该对大部分人安于现状感到高兴,而我更加高兴的是他们能够和平共处,能够进行交易和共同繁荣。
但我宁可死也不愿加入他们,就这么简单。
(或者更确切地说,此时此地,我真的这么认为。)
诀窍是保持移动,维持动量。不存在完全中立的区域,即便有,它们也小得不可能被发现,就算能发现,也很可能无法栖身,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随着吸引域内的条件改变而漂移。足够接近就足以过夜了,但假如我在一个地方住下,随着时间一天一天、一周一周过去,那么只要有任何一个吸引子具备最微弱的一丁点儿优势,它最终也会使我动摇。
动量,还有混沌。无论我们是不是真的因为互不相关的胡言乱语相互抵消而不必遭受彼此内心声音的荼毒,我的目标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信号中更持久、更连贯和更有害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地球的最中心,所有人类信仰加起来的总和将是纯粹而无害的噪声;但是在地表上,物理决定你不可能与所有人保持同等距离,因此我必须不停移动,尽我所能平均各种各样的影响。
有时候我会幻想前往乡野,过着愉快而清醒的孤独生活,住在机器人照管的农场旁,窃取我需要的设备和给养,种植我吃的所有食物。和玛利亚在一起吗?只要她愿意来;她有时候愿意,但有时候不愿意。有五六次,我们已经告诉自己,我们正在踏上这样的征途……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发现一条能够离开市区的轨迹,一条能够带着我们安全绕过所有相互干扰的吸引子的路径,但这也不足为奇:只有已经误打误撞沿着正确道路离开市区的人,才有可能确定地知道该如何离开市区,而他们不可能留下任何线索或传闻。
但有时候,我会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中央,问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逃进乡野,在我聋哑灵魂的沉默中迷失自我?
放弃毫无意义的游**,重新投向文明?为了繁荣、稳定性和确定性,吞下一套精心设计、自我肯定的谎言并被它吞噬?
还是继续像这样绕行,直到死去?
答案当然取决于我所站立的位置。
又是几辆机器人驾驶的卡车从我身旁经过,但我甚至懒得多看它们一眼。我把我的饥饿想象成一个物体——我必须背负的重量,并不比我的行囊更重——它逐渐从我的注意力中隐退。我让意识变得空白,什么都不去想,除了照在脸上的清晨阳光和走路的乐趣。
过了一会儿,惊人的明晰感逐渐笼罩了我。那是一种深入内心的平静,还有一种强烈的理解感。古怪的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理解了什么。我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体验到了洞察的喜悦,但没有任何希望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对什么的洞察?然而,这种感觉却挥之不去。
我心想: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兜圈子,而我被带到了哪儿呢?
带到了这个时刻。带到了现在这个机会,让我真正地朝着启迪迈出了第一步。
而我要做的只是继续走,一直向前。
四年来,我一直走在错误的道上——追寻名叫自由的幻觉,我的奋斗除了奋斗本身没有任何理由——但现在我看到了正确的方法,能把我的旅程转变为——
转变为什么?通向灭亡的捷径?
“灭亡”?根本不存在。只存在轮回,各种欲望的跑步机。只存在徒劳的奋斗。此刻我的头脑被蒙蔽了,但我知道只需要再走几步,真理就会变得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