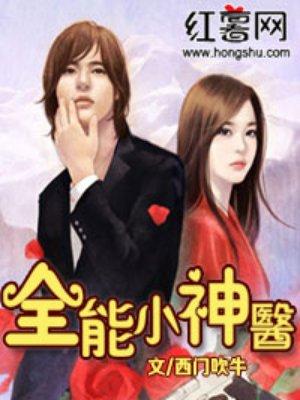文海阁>雾都孤儿 > 第四章 奥利弗获得别的身份初次步入社会(第1页)
第四章 奥利弗获得别的身份初次步入社会(第1页)
第四章奥利弗获得别的身份,初次步入社会
大户人家的子弟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倘若得不到优越的地位,无论这地位是实际拥有、复归享有[1]、指定继承[2]的,还是有望得到的,就会按照一般的惯例被送去航海。教区理事会效仿这一明智而有益的惯例,开会商讨是否可以把奥利弗·特威斯特送上一艘小商船,前往某个会严重损害健康的港口。这看起来是处置他的最好办法。也许哪天饭后,船长会玩笑开过头,将他鞭打致死,或者用铁棒砸得他脑袋开花。众所周知,在那个阶层的绅士中间,这两种消遣都是颇受欢迎且习以为常的。理事们越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就越是觉得此举好处多多。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为奥利弗提供生计的唯一有效办法,便是一刻也不耽搁地把他送到海上去。
邦布尔先生被派去进行各种先期调查,看能否找到什么船长需要无亲无故的服务生。此刻,他正要返回救济院报告调查结果,却在大门口碰到了承办本教区殡葬事务的索尔伯里先生。
索尔伯里先生个子很高,骨瘦如柴,手脚粗大,身着破旧的黑色礼服,脚穿打满补丁的黑色棉长袜,还有一双与其相配的鞋子。他长了一张天生就不适合笑的脸,但总体说来,他还是颇具职业风趣的。他脚步轻盈地走到邦布尔先生跟前,同他热情握手,脸上洋溢着内心的喜悦。
“我已给昨天夜里死掉的两个女人量了尺寸,邦布尔先生。”这位殡葬承办人说。
“你要发财啦,索尔伯里先生。”教区助理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插进殡葬承办人递过来的鼻烟盒里——那是一个高级棺材的模型,做工精致,小巧玲珑。“我说,你要发财啦,索尔伯里先生。”邦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用手杖友好地敲了敲殡葬承办人的肩膀。
“你这样认为?”殡葬承办人不置可否地说,“理事会出的价钱太少了,邦布尔先生。”
“棺材也很小啊。”教区助理笑答道,但笑得极有分寸,以免失了他教区大员的身份。
索尔伯里先生一下子被逗乐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接连不停地笑了好一阵子。“有你的,真有你的,邦布尔先生,”他终于能说话了,“不瞒你说,自从实行新的伙食制度以来,棺材确实比过去窄了些,也浅了些。不过,我们总得挣点钱啊,邦布尔先生。干透的木材价钱很高,先生。再说,铁把手都是通过运河从伯明翰那边运过来的。”
“没错,没错。”邦布尔先生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难处。当然,赚取合理的利润是无可厚非的。”
“就是,就是,”殡葬承办人应和着,“如果我在哪笔买卖上赚不到钱,哎呀,我迟早要从别的买卖上捞回来,你懂的——呵呵呵!”
“当然。”邦布尔先生说。
“不过我得说,”殡葬承办人接着被教区助理打断的话继续说下去,“不过我得说,邦布尔先生,我目前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不利的情况,那就是,死得最快的总是胖子。从前过惯了好日子,多年来从不拖欠税款的人,一旦进了救济院,总是最先垮下来。我跟你说吧,邦布尔先生,只要多用三四英寸[3]的料,就没啥赚头啦,对我这种需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就更是扛不住啊,先生。”
索尔伯里先生越说越气,好像自己饱受盘剥一样。邦布尔先生觉得让对方再说下去很可能损害教区的声誉,最好换个话题,而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奥利弗·特威斯特,就索性聊起了那孩子。
“顺便问一下,”邦布尔先生说,“你知道谁想要个学徒吗?救济院有个孩子,眼下就像套在教区脖子上的大石头——可以说就是一块大磨石[4]。条件可是相当优厚哟,索尔伯里先生,相当优厚!”邦布尔先生一边说,一边举起手杖指着头上的告示,在巨大的正体大写字母写成的“五英镑”字样上咚咚咚响亮地敲了三下。
“天啊!”殡葬承办人说,一把抓住邦布尔先生制服外套的镶金边翻领,“这正是我要跟你谈的事情。你知道——天啊,你的纽扣真精致呀,邦布尔先生!我还从没注意到呢。”
“是的,我也觉得很漂亮。”教区助理说,低下头,得意地看看装饰外套的大黄铜扣子,“上面的图案跟教区的印章一模一样——一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正在救援一个身受重伤的病人[5]。这是理事会在元旦早晨送给我的礼物,索尔伯里先生。我记得,第一回缀上这纽扣的时候,我去参加了半夜死在大门口的一个破产商人的死因调查会。”
“我想起来了,”殡葬承办人说,“陪审团宣布说,他‘死于受冻和缺乏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对吧?”
邦布尔先生点点头。
“陪审团好像就此事做出了特别裁判,”殡葬承办人说,“加了几句话,大意是如果当时救济委员——”
“呸!胡说!”教区助理打断了他的话,“要是无知的陪审团无论瞎咧咧什么理事会都认真对待,那他们准会忙翻天的。”
“千真万确,”殡葬承办人说,“他们确实会忙死的。”
“陪审团嘛,”邦布尔先生说着握紧了手杖,他情绪一激动就有这样的习惯,“陪审团里都是些目不识丁、俗不可耐、摇尾乞怜的卑鄙小人!”
“确实如此。”殡葬承办人说。
“无论是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他们知道的就那么一丢丢。”教区助理说,不屑一顾地打了个响指。
“谁说不是呢。”殡葬承办人赞许道。
“我鄙视他们!”教区助理脸涨得通红。
“我也是。”殡葬承办人附和道。
“我真希望让哪个自以为是的陪审团成员到救济院来待上一两个礼拜,”教区助理说,“理事会的规章制度很快就能灭掉他们的嚣张气焰。”
“别理他们。”殡葬承办人说,微笑着表示赞同,想要平息这位怒不可遏的教区职员正往上冒的火气。
邦布尔先生脱掉三角帽,从帽顶取出手帕,抹去额上因愤怒而渗出的汗水,又重新戴上帽子,向殡葬承办人转过脸,用缓和下来的口气问道:“对了,这孩子的事,你觉得怎么样?”
“噢!”殡葬承办人答道,“哎呀,你知道,邦布尔先生,我济贫税可是没少交的。”
“嗯!”邦布尔先生说,“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殡葬承办人答道,“我觉得,既然我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我就有权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得到好处,邦布尔先生,所以——所以——我想把那孩子领走。”
邦布尔一把抓住殡葬承办人的胳膊,将他领进了屋。索尔伯里先生同理事们密谈了五分钟,最后商定,奥利弗当晚就到他那儿去“实习”。对教区学徒而言,这个词的意思是,经过短时间的试用之后,如果师父发现该学徒不用吃多少饭,却能干不少活儿,就可以把他留下来用上几年,随意使唤。
那天晚上,小奥利弗被带到“绅士们”面前。他们告诉他,他当晚就要去一家棺材店当小工,如果他对自己的境遇有所不满,或者胆敢重返教区,就会被送到海上,那他就免不了会被淹死,或者被敲破脑袋。见奥利弗毫无反应,他们便一致宣称他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坏蛋,命令邦布尔先生立即把他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