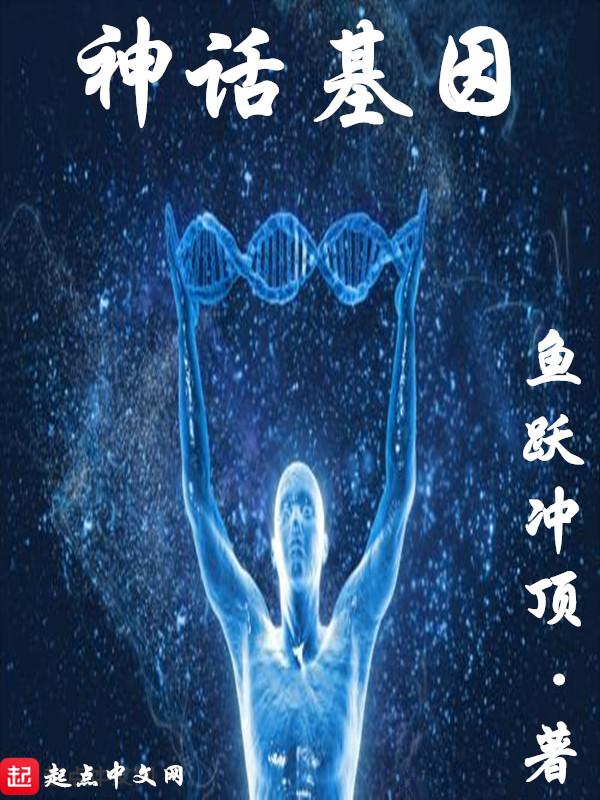文海阁>上海情人 > 29 病中了悟(第2页)
29 病中了悟(第2页)
乔姗姗掏出车子钥匙,走出两步,又回头说:“你给罗列打个电话,叫他赶到东方医院来。”
只见牛如山跟在后面,病怏怏地走到门口,面色苍白,非常难受。牛丽连忙走出去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
直到车开走,牛丽才进屋。撩开床单,露出罗列的脸,说:“出来!”
罗列一边往外爬,一边问:“车开走了?”
牛丽说:“乔姗姗让你赶紧到东方医院去。牛总病了。”罗列一听说老总病了,急着要走。一看包里,只有几十块钱。牛丽见状,说:带点钱吧,你得打的过去。”顺手拿出一把钱塞到罗列手里。
罗列说:“你一个人在家小心点。”说毕,亲了牛丽一口,大摇大摆地出门了。他感觉自己像个刑满释放的人,该是重新做人的时候了,每一块天空都特别美好。
罗列和乔姗姗的车几乎同时到达医院。乔姗姗扶着牛如山刚进急诊室,罗列就赶到了。牛如山在检查时,乔姗姗问罗列“这么快就赶到了?”
罗列说:“我一接到牛丽电话就往外跑。”
乔姗姗知道,到东方医院,罗列住得比他们要远得多,乔姗姗一路没有塞本,按理说罗列就应当后到许多。他们几乎同时到达,时间上是不对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速度与距离的关系。乔姗姗猜出来,罗列一定是躲藏在牛丽房间,才有可能紧跟在他们后面。但乔姗姗装作不知道,说:“你已睡了吧?”罗列一本正经地说:“已经睡过一觉了。刚刚醒来就听见手机响。”
牛如山得的是急性肠炎,需要住院治疗。乔姗姗时刻守着牛如山,把钱交给罗列,让他去交费,办理住院手续。一切手续办完,罗列又累得满头大汗了,今天是他出汗的日子,一次又一次的汗水已将衬衣反复泡过,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汗味儿。
他有些自惭形秽,又有自知之明,不敢离他们太近。
牛如山连续拉了五六次肚子,又伴着腹胀和腹痛,躺在**输液,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牛如山让乔姗姗回家休息,罗列在医院侍候他,乔姗姗非要留下不可。牛如山见乔姗姗焦急的样子,说:“我会死吗?”
乔姗姗说:“俗话说,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你是死不了的。”
牛如山说:“该不会是癌症之类的不治之症吧?听说肝癌也拉肚子的。”
乔姗姗说:“看你都说哪儿去了?你是肠炎,急性的。其实拉一拉肚子也好,就像排水管道一样,要经常疏通,以免有毒物质在里面存留。”
牛如山说:“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办?”
乔姗姗说:“那我就出家,做尼姑去。”
牛如山说:“那不可能,太漂亮的女孩是脱不了凡尘的。”两人说话的时候,罗列躺在**睡着了,并打起了鼾。牛如山看看他,说:“这小子好像很累了。”
乔姗姗说:“他也该睡觉了,再过一会儿天都亮了。”
牛如山有气无力地说:“你也躺在旁边睡吧,不能跟着我拖。”
乔姗姗摇摇头。她端把椅子放在牛如山病床旁边坐着,双手托腮,看着牛如山起伏的胸部,目光如水。乔姗姗问:“你好些了吗?”
“好些了,看来是死不了了。”
乔姗姗关切地说:“你痛的话,就说出来。说出来就会好。”
牛如山见她轻声细语的样子,很感动。他伸出一只闲着的手,抚摸着乔姗姗的脑袋,把她按在床沿上,轻轻地拍着她的头发,希望乔姗姗在他的安抚中入睡。一瓶液没输完,乔姗姗就睡着了。
乔姗姗睡着的样子像一首诗,头上放着牛如山的一只手,那是诗眼。
牛如山看到别人呼呼入睡的情景很羡慕。可他睡不着。他并不痛,可他却由此想到了死。他觉得疾病这东西确实奇怪,明明一副好好的身子,怎么就翻江倒海地拉起来,就这么一百多斤肉,无论如何是经不起拉的。几次厕所一上就拉空了。记得父亲死时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心里明白似镜。之后,他一度对死亡也是一副类似的态度。可现在一个小疾,就使他对死亡产生了莫大的恐惧。一方面因他身后有着巨大的家产;一方面眼前有着乔姗姗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一旦死了,这一切都将变成乌有。上帝对人类很公平,不管你是穷是富,疾病和死亡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年长年少,死亡的代价都是一样的,需要你付出毕生所得。
对于死亡的种种假设,使牛如山想到了乔姗姗说的一句话:你的钱太多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曾经觉得这话有些怪。天下没有嫌钱多的人。在上海的穷人里面,他是富翁。亿万资产的确是能用几辈人的。可在上海的有钱人里面,他只是小富。现在他觉得,乔姗姗的话提醒了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假如眼睛一闭,再多的钱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了。
天亮时,乔姗姗醒来,说:“你还没睡?”
牛如山说:“睡不着。我在想,假如我得的不是肠炎而是绝症,那该是另一种情形了。”
乔鳙姗说:“你别胡思乱想。”
牛如山说:“等我病好了,我给你一百万块钱,你拿去做点事。”
乔撕旖说:“做什么事?”
牛如山说:“做一点对社会对你我都有益的事。”
乔姗姗说:“你是嫌钱太多了?”
牛如山说:“那倒也不是。只是觉得,有许多人太需要钱了。我们一天的费用,有些人可以过一个月,甚至过一年。”乔姗姗说:“我不敢要这笔钱。”
牛如山说:“这不是给你的,是让你拿去做事的。”
乔姗姗说:“你让我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