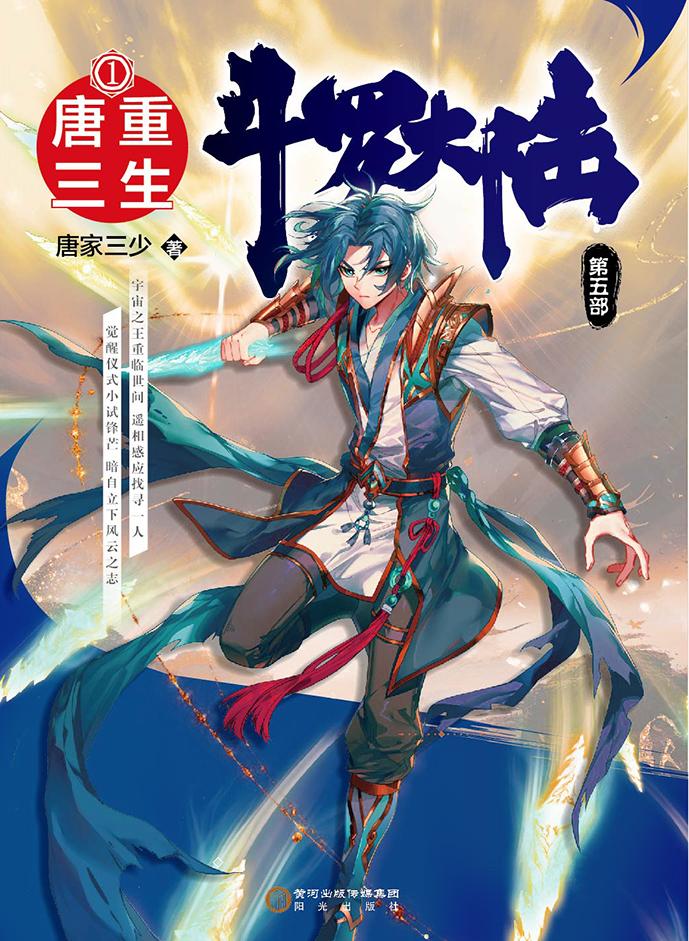文海阁>我来大宋搞审计 > 第95章 帝指要惊煞辽將(第2页)
第95章 帝指要惊煞辽將(第2页)
“將军此言差矣。”
他转身对李默道,
“取笔墨来。”
当晚的驛馆被暮色笼罩,辽骑们围著篝火烤肉,铜壶里的奶酒咕嘟作响。
萧挞凛正擦拭弯刀,忽然见李默抱著捆竹简和一卷白麻纸走进章衡的房间,油灯的光晕透过窗纸,映出章衡俯身书写的身影。
“將军,那宋官在画什么?”
亲卫凑过来,手里还攥著白天那张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草图。
萧挞凛皱眉望去,窗纸上的影子时而勾勒山脉,时而標註河流,动作利落如挥剑。
“装神弄鬼。”
他冷哼一声,却忍不住起身,借著查看防务的名义,悄悄走到窗下。
“此处需註明,黄河在孟州以下为『地上河,河床高於堤外平地丈余,汛期需格外防备。”
章衡的声音清晰传来,
“还有江南的圩田,需画出『四横三纵的灌渠走向,这是范仲淹在苏州治水时创下的法子。”
萧挞凛扒著窗沿的手指猛地收紧。
他在宋辽边境征战多年,只知宋军善守,却不知他们连江河走势、农田水利都摸得如此透彻。
正听得入神,房门忽然开了,章衡举著卷刚画好的地图站在门口,油灯的光在他眼中跳跃。
“萧將军既然感兴趣,何不进来一观?”
驛馆的堂屋被临时腾空,白麻纸在八仙桌上铺开,竟有丈余见方。
章衡手持狼毫,蘸著硃砂在纸上勾勒:
“此图名为《帝指要》,取『帝王经略,指掌要地之意。”
他笔尖点向东北,
“此处是幽州,辽称南京,唐时为范阳节度使治所,安史之乱便发源於此——其得失关乎河北安危,故图上特意用硃笔標出周边八关。”
萧挞凛的目光被牢牢吸住。
图上的山川河流比辽廷藏的《五代疆理图》精確百倍:
太行山脉的七十二陘一一標註,每条陘的宽窄、坡度都有说明;
黄河的九曲十八弯用墨线细细绘出,关键渡口旁还注著“春汛水深三丈,冬涸可涉”;
甚至连江南的湖泊港汊,都標著“可藏战船百艘”“利於水战”的小字。
“这……这是如何画成的?”
辽骑中的老兵忍不住惊呼,他曾隨萧挞凛攻打过瀛州,图上標註的“瀛州城墙高五丈,外包青砖”,与他亲眼所见分毫不差。
章衡蘸了点墨,在图中央画了个圆圈:
“汴京乃天下之中,东经汴水通江淮,西循黄河连秦晋,北溯永济渠达幽燕——故需在此囤积粮草三百万石,方能支撑四方军需。”
他忽然转向西北,
“萧將军请看,灵州虽偏远,却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其地盛產盐铁,故西夏屡犯不止。”
萧挞凛的心猛地一沉。
灵州是辽与西夏爭夺的要地,他上个月还在此与西夏人谈判,图上竟连“西夏覬覦盐池”的批註都有。
“大人怎会知晓这些?”
“《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