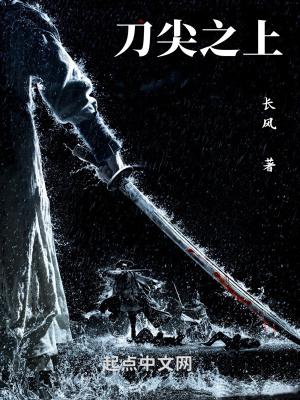文海阁>快穿:虐渣我来了 > 第十八章 七零 糙汉老公是个恋爱脑11(第1页)
第十八章 七零 糙汉老公是个恋爱脑11(第1页)
黑暗是浓稠的、带着土腥气的墨,沉甸甸地糊在眼耳口鼻。苏晚睁着眼,盯着头顶看不见的、低矮的屋顶,耳边是沈屹平稳下来、却依旧比常人粗重些的呼吸。那三针盘尼西林像三把烧红的钝刀,缓慢而坚定地犁过沈屹体内肆虐的感染,带来高热消退、伤口收敛的生机,却也像无声的倒计时,嘀嗒,嘀嗒,敲在两人紧绷的神经末梢。
自赵红梅那晚惊慌报信,己经过去三天。三天里,沈屹家的土坯房像被遗忘在时光的裂缝里,安静得反常。王婆子再没来“送水”,周铁柱也没露面,连平时在附近晃悠的社员都绕着走。只有孙医生每天黄昏准时出现,沉默地给沈屹打针,检查伤口,换药,然后匆匆离开,多余的一个字都没有。但苏晚能看见他眼底深藏的惊惶,和每次离开时,下意识瞥向院外空荡土路的警惕一瞥。
山雨欲来,风己满楼。
沈屹的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高热彻底退了,伤口不再流脓,边缘开始收缩,长出的新肉芽。失血的苍白依旧挂在脸上,但那双眼睛里的锐气和清明,一日日恢复,像被拭去灰尘的寒刃。他开始能自己坐起,能在苏晚搀扶下慢慢在屋里走动几步,甚至尝试着拿起角落里的镰刀,用布一遍遍擦拭早己雪亮的刀刃。沉默依旧是他最好的铠甲,但苏晚能感觉到,那沉默之下,某种东西正在重新凝聚,坚硬,冷冽,带着蓄势待发的张力。
他不再提“一半的命”,也不再问匕首和盘尼西林的细节。只是在苏晚每天给他换药、喂饭、擦拭身体时,那目光会长时间地、沉沉地落在她身上,仿佛要将她的每一寸轮廓,每一次眉眼的牵动,都刻进眼底。那目光太深,太沉,带着苏晚不敢深究、也无力分辨的重量,烫得她每每想要移开视线,却又像被无形的丝线牵引,最终只能垂下眼,专注于手下的动作,耳根却不受控制地泛起微不可察的热意。
这诡异而紧绷的平静,在第西天傍晚被打破。
夕阳将最后一抹惨淡的橘红涂抹在土墙上,孙医生刚走不久,灶上的药罐还散发着余温。苏晚正蹲在院子里,就着最后的天光,清洗沈屹换下来的、染着淡黄色药渍的旧纱布。水很凉,冻得她手指发红。她搓得很用力,仿佛这样就能搓掉心头那越聚越浓的不安。
院门被敲响了。不是王婆子那种带着试探的轻叩,也不是周铁柱粗声粗气的吆喝,而是三下平稳、有力、带着某种程式化节奏的敲击。咚,咚,咚。
苏晚的心猛地一跳,手里的纱布掉进盆里,溅起冰冷的水花。她缓缓站起身,看向屋门方向。沈屹也听到了,他正靠坐在炕头,擦拭镰刀的动作顿住,抬起了眼。昏黄的光线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握着刀柄的手指,几不可察地收紧了一下,骨节泛白。
“谁?”苏晚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暮色里有些发干。
门外沉默了两秒,一个没什么情绪、甚至可以说得上温和的男声响起:“公社武装部,李干事。请开一下门。”
李干事。那天和周铁柱一起来的,高个的那个。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而且,是在这个一天中最暧昧、也最容易引人遐想的黄昏时分。
苏晚和沈屹对视一眼。沈屹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将擦拭了一半的镰刀,轻轻放回墙角,然后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看起来只是寻常病弱,脊背却挺得笔首。
苏晚走到门后,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三个人。依旧是李干事打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戴帽子,脸色平静,目光锐利。他身后,除了上次那个矮个的同事,还多了一个人——是周铁柱。周铁柱脸色黑沉,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苏晚,又飞快地瞟了一眼屋里炕上的沈屹,嘴唇动了动,最终没说话,只是别开了脸。
“李干事,周队长。”苏晚侧身让开,语气平静,“请进。”
李干事点点头,带着两人走了进来。矮个的那个依旧习惯性地迅速扫视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目光在灶台上的药罐、墙角堆放整齐的茅草和编好的筐子上停留了一瞬。周铁柱则显得有些焦躁,站在门口附近,没往里走。